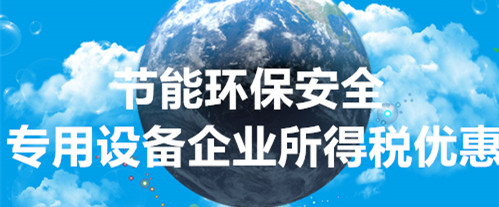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的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治理研究:现实困境、域外经验及修补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治理研究:现实困境、域外经验及修补路径水污染治理 城市污水处理 生活污水水处理网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密集建立、城镇的规模扩张、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
水处理网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密集建立、城镇的规模扩张、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水污染治理是新時代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贯彻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呈现出治理设施薄弱化、治理目标差异化、治理方案任意化和治理体系简单化的特点。作为发展起步较早、治理经验较多的世界三大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水污染治理上采取了设立统一机构发挥协调功能、制定法律提供法制保障、重视社会力量健全治理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和长远规划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城市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大湾区水污染的协同治理机制、健全大湾区水污染的多元治理体系,为大湾区早日建设成为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主流湾区创造良好生态环境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包括肇庆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惠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门市等九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整个区域总面积约为5.6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00万,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P113)截至2018年,大湾区的GDP总值已经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成为继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之后又一个世界级的湾区。无论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还是日本的东京湾区,都成了世界各大企业争相入驻的聚集地,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样,大湾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其地域面积广、经济体量大、发展速度快,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引领了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但经济的繁荣也附带了大湾区水污染的负面结果,既破坏了生态环境的稳定结构,更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动力。健康的水环境和优质的水资源,是大湾区实现快速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关注大湾区水污染治理这一议题,分析目前大湾区水污染治理的现实问题,考察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水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探索如何进一步完善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应当是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一、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的基本概况
大湾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拥有着引导力,受到了相当多大型企业的青睐,这些大型企业纷纷进入大湾区,希望能够搭上大湾区未来高速发展的“顺风车”。于是大湾区的开发力度被不断加大,给大湾区经济发展带来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大湾区水域内河道交错密布,形成了复杂的网状交叉,密集的生产企业建立、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都造成了各类生产、生活污水的多向性汇集,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水污染,这种由点及面的水污染扩散,使大湾区水污染的治理更加复杂,治理任务也更加艰巨。[2](P117)根据历年发布的《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来看,珠江广州河段、深圳河、东莞运河、龙岗河、坪山河常年处于重度污染的状态中,近十年来都没有得到过明显的改善。
《2017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7年珠江口、汕头港、湛江港等近海海域的海水质量多劣于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换而言之,这些地区的海水水质已经低于我国海水质量的最低标准。造成其水质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超标会导致海水水质的富营养化,使藻类植物过度生长,而其他的海洋生物则由于缺乏氧气而大量地死亡。[3](P704)如近年来我国近海海域频发的“赤潮”,都与此类污染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藻类植物与海洋生物大量死亡之后,就会使其所在的海域遭受更为严重的有机污染,如近海海域的海水发黑、发臭等现象。[4](P264)同汕头港和湛江港相比,珠江港的海水污染程度更深、影响面积更大,包括澳门在内的广大近海海域都在其污染范围之内。连接大湾区主要城市的珠江与深圳河,在2017年向其邻近海域排放污染物总量为327.91万吨,其中位于珠江口水域上游珠江河道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为325.27万吨,对处于其下游水域的中山市、深圳市、珠海市、澳门等地都造成了较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于2016年,珠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了122.51万吨,其中绝大部分污染物的化学需氧量浓度比较高。一般来说,化学需氧量高代表水域中的有机物污染较为严重,不但会对水域中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会以毒素的形式对人体产生危害,在医学上这些毒素往往具有致癌性和致畸性。从广东省2017年对各个入海排污口的统计数据来看,有50.7%的排污口属于市政排污、32.9%的排污口属于工业废水排污入海口,其余为各类排污河入海口。在市政排污中,就有43%的入海口所排放的污水超标,这也说明近年来由于东南沿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其人口吸纳能力大幅增长,周围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给水污染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除此以外,大量固体垃圾的填埋所产生的渗滤液也对水环境造成了不小的污染,除了珠三角地区每年排放数量巨大的固体废物之外,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固体废物的产生总量也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香港特别行政区仅在2017年就产生都市固体废物575万吨,其中工商业固体废物为158万吨,较2016年增加9.5%。1澳门特别行政区2017年弃置的城市固体废物量为510 702公吨,与2016年相比呈上升趋势。2
针对这些水污染问题,各相关部门也相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治理,如签订一系列协同治理的书面协议3;设立跨境合作的“环保合作小组”4;对重点水域的污染情况进行严密监测;收集大量的污水排放数据观测水质的变化趋势;多次进行多点巡查;以高压态势对环境保护进行执法等。但目前的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满足大湾区水污染治理的现实需要,在大湾区水污染的治理实践中仍然面临许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有效解决。
二、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污染治理设施的薄弱化
与大湾区城市群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类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2017年,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在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反映环境保护督察情况时,指出广东大部分地区水污染问题突出,治理现状与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如广州市在“十二五”规划中拟修建1884千米的污水管网,但通过检查发现实际上只完成了总工程目标任务的31%。深圳市市建工程中污水管网建设缺口约为4600千米,导致深圳市的污水收集率不足50%,有超过一半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流入河道。[5](P45)中山市2012年以来投资约21亿元建成949千米管网,这些管线是为了实现“雨污分流”工程1而建设的,但由于工程整体质量状况并不理想,工程建成之后的管理工作也有待改善,因此造成了城市污水收集、处理占比较低,未达到预期效果。
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已经严重制约了大湾区推进水污染治理,其中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财政投入差异是一大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主要依靠自行筹划和解决,而城市排污处理基础设施的建设,既耗资巨大又难以在短期内看到明显的经济效益,本地区花费巨资修建的各类污水处理设施却不能给本地区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显然容易导致城市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建设动力的不足。[6](P267)再者,上下游城市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甚至有些城市和地区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大湾区中,广州、东莞、江门等城市处于整个大湾区的上游水域,深圳、珠海、中山、香港以及澳门等城市和地区则处于大湾区的下游水域,而排放污染物流入近海海域最多的珠江就处于整个大湾区的上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各自在水污染治理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不同,那么对于区域内一些投入动辄过亿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自然难以得到顺利建立。就广东全省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来看,大湾区内城市群的建设情况相对较好,但粤西北、粤东地区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滞后、建设进度缓慢、资金缺口大,许多工程未能按时按质完成而效果不理想。
(二)污染治理目标的差异化
大湾区是由九个沿海城市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所组成的东南沿海城市群,这种基于多个行政区域交错形成的水污染治理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客观上存在着多个行政区域的差异性和复合性需求。经济较为落后的城市或地区,希望能够大量吸引资金和技术,兴建各类企业和工厂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完成地方的经济增长任务。“经济发展高于一切”是这类城市和地区的普遍共识,GDP的增长成为政绩考评的主要标准,在这种理念和制度的诱导下,一些地方政府忽视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缺少区域长远利益的考量,对于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污染企业实行地方保护主义。[7](P57)而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则更希望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能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下。经济利益方面的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之后,这类城市和地区更多关注的是生存环境的改善以及对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对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关注,一般来说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也较多、力度也更大。
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由于思想认识、地理位置、环境资源等不同,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别,尤其在大湾区内还有两个发展起步早、发展时间长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在渡过了经济转型期之后便大力发展城市旅游业与生态经济2,这都与内地许多城市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理念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冲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各地政府之间对于环境保护标准认识以及环保目标设立的巨大差异,比如在大湾区各城市中,香港和澳门在环保标准和环保目标的设定上,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把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污染标准纳入自身的环保目标设定中来,并对污染物的排放实行强度较大的管制。
与之相比,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对于污染物的排放管理,则要考虑到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在这些城市的污染管理中,所体现的往往是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对于污染物的排放则采取的是拉长治理时间并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1中,开篇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并且对各个时期分别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到2012年,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80%左右,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0%;到2020年,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90%以上,工业废水排放完全达标”。可以看到,珠三角地区的污染治理方式是“且行且治”,既不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也希望能够形成一个逐步改善直至扭转严重污染局面的良性发展趋势。但我国很多省市都在实行不同的废水排放标准和水质标准,即使是达标排放的大量工业废水中也仍然含有一定浓度的污染物,这些工业废水排入河流,也造成了水污染治理成效不明显的现状。
(三)污染治理方案的任意化
大湾区各地政府之间为了协调和解决水域内存在的污染问题,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政府间也不断地签订了各类污染治理合作协议以及污染治理计划2,这些合作协议以及治理计划的产生,客观上确实对水污染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促进了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与大湾区整体的治理需求还有距离。因为这些协议与计划实际上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对协议各方的约束力也十分有限,支撑协议以及计划各方履行承诺的基础,往往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与高层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一旦遇到各方協议中的重要高层离任,就面临着协议被废止的风险,这种合作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复杂的、长期的水污染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另外,这些协议和计划对于各地之间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划分也是不明确的,导致了现实中存在打不完的“水官司”和理不清的“糊涂账”。对于大湾区这种区域性水污染而言,往往下游区域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上游区域则经常是水污染的主要责任者,但相对而言却受水污染影响较小而经济获益最多。在这种情况下,下游区域必然希望“谁污染、谁负责、谁治理”,而上游区域由于利益的驱使则更多地希望以“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方式来对水污染进行治理,这样既可以保住企业靠污染获得的经济利益,又不必承担被污染水域治理的责任与经济压力,上下游之间便互相推诿扯皮,从而形成了“上游获利、下游转移、群众受害”的不利局面。[8](P173)
随着我国对于环境保护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环境保护中水污染治理的精细化,与保护水资源、治理水污染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关于预防与处置跨省界水污染纠纷的指导意见》等。但这些法律法规都过于笼统和宽泛,对于一些共性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但我国国土面积广阔、河流众多,水文形态更是多种多样,甚至每个流域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问题3。这些流域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仅仅以宽泛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或者指导性文件是无法彻底解决的,所以我国也开始针对不同流域的特点相继展开了立法工作,如制定《长江保护法》等。与长江、黄河流域相比,大湾区城市群拥有6000多万的人口,近年来广东省人口流入量每年接近200万人,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入珠三角地区,可以说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最具有活力和生机的地区之一。除此以外,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大湾区凸显其重要地位的主要因素,将大湾区打造成我国的“曼哈顿+硅谷”完成与世界范围内高科技产业的对接是大湾区未来的发展蓝图。可见大湾区将会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大新引擎,从这一角度来看,围绕大湾区水污染治理协同立法建设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其未来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是极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四)污染治理体系的简单化
大湾区的水污染问题涉及领域多、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除了政府要加大治理力度以外,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激发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能动作用,可以更好地解决治理难题。而我国在水污染治理体系的建立上,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治理层次的单一性,这一点在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中也较为明显。水污染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将对水污染的治理与监督完全推给地方政府或者环境保护部门,显然是忽略了公众以及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巨大活力。客观上,政府部门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来对水污染进行治理,不但会造成水污染治理工作“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还容易给一些腐败官员与污染企业进行权钱交易滋生土壤和创造机会。
一个健康完善的水污染治理体系,应当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严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政府主导、环境保护部门主抓、污染企业履责、社会力量与媒体共同监督、环保公益组织与公众积极参与的有机整体。但现实中,政府对于环保社会组织的限制颇多,导致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得不到相应的合法资格,再加之各类环保社会组织的经费问题、专业能力的提升问题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又加大了其积极参与水污染治理的难度,使这些原本应当在水污染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环保社会组织难以实现自身价值。社会组织具有两大基本特性——“非政府性”与“非营利性”,许多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都是不固定的,日常活动的经费都比较紧张,只有少数由政府发起建立的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政府划拨资金以及由政府向其购买相关服务的方式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在2015年广东省环保社会组织的调查中显示,全省较为活跃的环保社会组织有157家,并且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三地,而来自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组织为54家,其中约有90.7%的环保组织的主要活动都与水污染治理和海洋保护有关,很多组织成员都是身受其害的普通民众,既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也没有稳定的活动资金来源,导致这些环保社会组织在水污染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三、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治理的域外经验
(一)东京湾区水污染的治理措施
东京湾区由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琦玉县所组成,包括东京、横滨、川崎、千叶、横须贺等几个大中城市,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区,占日本总面积的3.5%。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东京湾区作为日本发展经济的重要区域迎来了跳跃式的大发展,很快就成了日本与国际金融、商贸进行对接的中心区域。许多大型企业纷纷进驻东京湾区,逐步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基地,这些生产型企业大量排污,对东京湾区的水质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海湾的营养盐负荷过高且海水自净作用减弱,使得水污染日益严重,各类由于水污染而造成的健康问题层出不穷。[9](P15)但由于东京湾区城市群水域相互交错,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导致水污染治理一直未有起色。针对这种情况,1970年日本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统一了废水排放的标准,对企业废水排放的浓度和总量控制以及相应的排水设施建设等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并对未达到标准的废水排放行为的惩处措施都进行了法律上的规定。随后,日本又于1971年制定了《公用水面环境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针对公共水域的污染问题而设定的,所有向公共水域排放的废水都必须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1973年日本为防止东京湾区工业污染严重的情况再次出现,又专门制定了一部《港湾法》,该法强调在港湾的开发建设过程中,要把港湾环境保护和治理作为一个重点内容进行总体评价,以往那种不计后果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的港湾开发模式被日本政府坚决制止。至此,日本水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建立起来,随后日本又针对水污染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些法律上的补充,如1989年的地下水污染防治、1990年的生活污水治理以及造成水污染的另一大元凶——渗漏事故处理等。
在东京湾区水污染的治理中,城市群成员间的各类协调和磋商并不是各城市之间独自发起的,而是由日本国土交通省下属机构成立的“东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来负责协调和平衡的。当东京湾区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产生纠纷和分歧时,“东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就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调停,由于其具有官方背景,所以在东京湾区的各城市中具有权威性。但在东京湾区城市群中一些关于共同事务(包括“水官司”)的咨询、评估、决策和评判,则是由智库来主导的,再由“東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来保障执行,甚至日本政府都不能随意干涉。
(二)旧金山湾区水污染的治理措施
旧金山湾区占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是美国西部第二大都市区,也是美国著名的金融科技中心。湾区内多个城市都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如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等。早在19世纪中期,旧金山湾区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美国的物资流通核心区域,各类商品在旧金山湾区汇集再被运往世界各地。20世纪后美国工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各种工业生产企业同样开始在旧金山湾区聚集,自然也对湾区的水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为了能够更好地整合湾区内各个城市的力量来共同治理污染问题,旧金山湾区成立了旧金山湾区机构总部,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ABAG)、海湾保护和开发委员会(BCDC)、大都市交通委员会(MTC)等多个核心部门,来专门协调整个旧金山湾区区域内的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
在旧金山湾区的水污染治理中,美国颁布实施了《清洁水法案》《史蒂文斯渔业养护与管理法案》《加利福尼亚波特科隆水质控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在机构设置上,除了海湾保护和开发委员会之外,还有例如拯救海湾1等这样的公益机构进行协助共同治理。除此之外,旧金山湾区水污染治理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注重该地区多元化力量的参与,使公众对于湾区的建设拥有较为广泛的话语权。在旧金山湾区的治理方案中,不但有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的专家来进行科学的评估,也有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各自表明态度和表达观点,公众也有相应的权利参与其中并针对污染问题反映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由官方、智库、利益相关者以及普通民众所组成的多元化规划和治理体系,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参与其中。在这种公开透明的体制下,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兼顾了多方的共同利益,彻底扭转了水污染严重的不利局面,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完成了由传统工业发展向科技产业转化的区域目标,使旧金山湾区成为世界著名的“科技湾区”。[10](P101)
(三)纽约湾区水污染的治理措施
纽约湾区是美国东海岸的航运枢纽,其连接着美国内陆五大湖区的运输航道,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纽约湾区总面积为33 484平方公里,橫跨纽约、新泽西以及康涅狄格三个州,湾内共有31个郡县,多个行政区域交错使纽约湾区在协调各州、各个城市之间的利益以及相关事务上不得不采取统一管理的方式,来整合纽约湾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和力量。于是纽约湾区成立了区域规划委员会(RPA),来保证湾区内的各项规划和建设能够整齐划一。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高效、集中、统一的规划和建设,已经成为纽约湾区能够百余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最主要原因。
与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一样,纽约湾区的发展历程也同样有着生态环境恶化、水环境遭受污染的经历。哈德逊河是纽约湾区最重要的河流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哈德逊河中,导致了有毒化合物聚集、鱼类死亡、河水发臭等严重污染问题。在充分认识到严峻的现实问题后,纽约湾区严格遵守《清洁水法案》,开始加大力度进行废水处理,并且建立了哈德逊河国家河口研究保护区,同时引入社会各方机构合作治理。20世纪末期,区域规划委员会重新对纽约湾区的发展进行了规划,把湾区中心进行了外扩,提高了对卫星城建设的投入力度,将污染问题化整为零,减轻湾区核心地区的污染压力。2013年,纽约州颁布了《污水排放知情权法案》,进一步规范了生活污水溢流现象,根据该法案的规定,生活污水溢流必须在2小时内通知纽约州环保部,4小时内通知公众。[11](P1090)2014年,纽约州在清理哈德逊河底泥沙的基础上,又通过了哈德逊河河口生态环境恢复计划。经过一系列的综合治理,哈德逊河已经成为大西洋沿岸最清洁、生态环境最好的河口之一,纽约湾区的水污染问题也得到了有效治理,摆脱了严重污染的状况。
(四)三大湾区水污染的治理经验
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的水污染治理,都是属于横跨多个行政区域而进行的跨区域治理。跨区域治理不但困扰着美国、日本等这样的发达国家,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是水污染治理工作中的难题。通过考察三大湾区水污染的治理措施,可以辩证地总结出一些可供大湾区借鉴的成功经验。
可以发现,世界三大湾区水污染的治理措施存在着如下一些相似之处。(1)设立相应的统一管理及协调机构,虽然因为各个湾区各自国情以及体制不同等原因,这些机构的名称、层级、职务等各有区别,但其都在湾区水污染治理乃至整个湾区发展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管理和协调功能,实现了湾区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这种权力上的制衡使湾区的发展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使湾区内因行政区域交错所造成的各种冲突迎刃而解。(2)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有国家立法,也有地方立法,但都及时扭转了在湾区水污染治理工作中面临的部门多、变数大、无法可依的艰难局面,并且又根据实践的需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不断补充完善这些法律法规,使其不断专门化和精细化,为水污染治理提供充分的法制保障。(3)积极推动公众参与,加强地区间的协商合作,重视及充分发挥政府、环保社会组织等社会各界的力量,建立一个较为完整和严密的多元化治理体系,也是三大湾区治理水污染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诚然,世界三大湾区发展至今,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水污染问题,甚至在治理进程中也曾有过一些反面教训,但较之于三大湾区而言,大湾区发展时间较短,相应的发展规划以及水污染治理体系尚不健全,以上这些成功的治理经验仍可供借鉴,有利于大湾区尽快地根据自身实践构建起科学的湾区规划和水污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改善大湾区水污染严重的状况,促进经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四、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治理的修补路径
(一)加强城市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
良好的水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是大湾区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要对标世界三大湾区,成为对世界经济具有引导作用的大湾区,必须要具有相应完善的水环境基础设施。水污染问题可以制约甚至阻碍大湾区的整体发展,所以在大湾区城市群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环境税收和各项污染企业的赔偿金与处罚款项务必做到专款专用,加强治污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可以通过将各地排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情况与各地政府政绩相挂钩的方式来提升各地政府对于排污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除了要增强各地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外,还要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各地政府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之余,也要更多地寻求社会资本的支持,通过提升和保障相关收益等方式来吸纳更多资金投入水污染治理的事业中来。对于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要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充分发挥支持水污染治理榜样的力量,这样不但可以将各地政府治理水污染的决心广泛地传递给社会各界,更能够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事业中来。
另外,对于以往大湾区水污染治理中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缓慢、城市群管网建设滞后而且质量不合格不达标的问题,要通过对目标细化并明确相关负责人要承担的具体责任来着手解决,对于没有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的,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目前大湾区城市群存在着已经按时完成了污水处理建设目标,但使污水处理发挥作用的管网还有巨大缺口的问题,而且工程质量不高,并且很多已经建设好的管网无法正常使用,成为“断头管”“僵尸管”,使前期对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投入无法转化为实际收益。针对这些情况,可以从抓“雨污分流”建设使用的实际效果入手,对于影响系统正常运转的原因要摸清和重点解决,使用中存在技术问题的尽快攻克解决,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严肃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另外,也可以尝试实行对大湾区上下游水污染关联城市设立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运转的“互助小组”,由下游城市组建工作组对上游城市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及运转状况进行评估,上游城市也可以组建工作小组随时了解下游城市的设施建设和使用状况,并可直接与中央环境督察组进行沟通,反映情况和说明问题。通过这样互相监督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扎扎实实地建设和管理,使城市群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真正地运转起来,有效避免大湾区城市群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成为应付上级下达任务的“面子工程”。
(二)完善大灣区水污染的协同治理机制
上下游、各区域、各城市之间缺乏协同,各自都只关注自己范围内的状况,进而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是制约大湾区水污染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12](P277)而造成水污染治理不联动、不协调的首要体现,就在于大湾区内缺少统一的区域协调机构。上述世界三大湾区中,都成立了主管湾区协调以及发展规划工作的专门机构,无论是东京湾区还是美国的两个湾区,都把湾区建设的决策权和规划权进行了统一,保证了湾区整体规划和建设的一致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湾区建设和规划的权力被集中以后,那么湾区内各个城市才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被片面地分割出来各自为政、多头管理、权责不清,以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式来对待水污染治理。水污染是大湾区内所有城市的共同问题,需要权力让渡与相互协作、统一规划与协同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一旦被割裂后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一个城市的问题得以解决后引发另一个城市的问题,旧的问题得以解决后引发新的问题,如污染问题转化成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转化成社会问题等。基于此,可以将大湾区内的区域协调权力与规划权力集中统一之后再进行科学配置,分别由相应的协调机构以及科研机构承担具体职能。对于协调机构的定位,可以借鉴三大湾区的成功经验,设立一个超区划、跨领域的水污染协同治理委员会,并下设各个专门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中,可以由大湾区各城市按比例委派,领导人由中央政府委派。[13](P11)对于科研机构的定位,可以由科研机构来对大湾区的整体发展进行规划,对于水污染等问题进行全局性的分析和评估,从而得出最有利于大湾区发展的最佳方案,交由大湾区各相关城市进行讨论与磋商,各城市可以表达观点和主张并说明理由,但最终决策权应当由大湾区的协调机构来掌握,并有强制力保证协调机构的决策能够得到顺利执行。
同时,需要认识到造成水污染治理不联动、不协调的根本体现,还在于大湾区内缺乏统一完备的法律体系。大湾区水污染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寻求一个统一的规则,这一规则能够明确各方治理主体之间的责任和权限,使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配置等逐步实现稳定化、规范化、制度化。[14](P56)粤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和相关法律程序均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在水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冲突和矛盾,影响到水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所以,应当以大湾区的水污染现状和整体发展规划为基础,协同制定完善精细化的法律法规,建立一套适用于大湾区三地的治理指标,统一大湾区的废水处理排放标准,并对整个湾区的废水排放总量和浓度进行控制和调节。重视差异、区别对待、协同立法的方式,可以避免出现大湾区内城市之间的法律规范冲突,防止各城市出现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法制化。[15](P69)对于大湾区的立法活动,应当由大湾区的协调机构主导,聘请法学专家以及大湾区内研究相关发展问题的专家,再由各地政府分管水污染治理的负责人,共同组建专门委员会集中研讨,并向公众广泛征集立法意见,使大湾区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框架能够早日建立起来。[16](P62)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不断根据实践发展要求进行更为细致的补充和完善,从而建立起一套适合大湾区整体水环境特点的水污染治理法律体系,使整个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纳入一体化、法制化的轨道中来。
(三)健全大湾区水污染的多元治理体系
大湾区水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问题。针对目前大湾区水污染治理中因政府主导和行政分割等导致的治理体系单一化、简单化,应当进一步健全水污染的多元治理体系,构建起一个“政府统领、企业实施、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的、立体化的水污染治理格局。[17](P30-32)世界三大湾区水污染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建立了多元化的水污染治理体系。无论是日本的民间智库,还是美国的各类环保社会组织,都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众参与是符合环境管理特点的富有成效的制度,旧金山湾区为了保证公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湾区水污染治理的事务中来,还制定了法律程序以及采取了相关权利保障措施,鼓励环保社会组织增强专业能力,政府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与其展开合作,共同参与湾区水污染治理。
健全大湾区水污染的多元治理体系,可以借鉴三大湾区的这一成功经验,加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信息互利互通,促进各个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各个治理主体不仅是水污染治理的受益者,更应当是水污染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忠实践行者。协调机构主要以全局的高度对整个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工作进行全面和细致的规划,并负责平衡各城市、各主体之间的治理工作关系;政府加强水管理的公共职能,保障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水污染治理工作顺利推进;企业严格遵守生产规范和排放标准,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公众积极参与水污染治理,减少家庭污染排放,并对治理规划以及建设实施情况进行建议和监督。
除此之外,还应当充分重视和发挥好新闻媒体和环保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是大湾区水污染治理工作向社会公开的桥梁,所以新闻媒体应客观真实地反映公众的呼声和意见,帮助公众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渠道,对于水污染治理中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新闻媒体也要大胆发挥报道督促作用,使治理工作尽量公开化、透明化。环保社会组织在水污染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样不能被忽视,应当进一步实现环保社会组织的价值,扭转环保社会组织在水污染治理中参与积极性不高以及专业能力不强的局面。对于协助政府部门对污染企业进行监督和调查,并取得一定成效的环保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设立水污染治理资金、污染企业赔偿金以及罚金提取一定比例的方式来进行奖励,使优秀的环保社会组织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并通过这些资金来吸引人才、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以更加完善的服务能力来协助大湾区的水污染治理工作,这对于政府部门的水污染治理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参考文献:
[1] 覃成林,刘丽玲,覃文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战 略思考[J].区域经济评论,2017(5):113-118.
[2] 王玉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合作的回顾与展望[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17-126.
[3] Anderson D M,Glibert P M,Burkholder J M. Harm- ful algal blooms and eutrophication:nutrient sources, composition,and consequences. Estuaries,2002,25(4): 704-726.
[4] Codd G A,Morrison L F,Metcalf J S. Cyanobacterial toxins:risk management for health protection. Toxi-col- 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2005,203(3):264-272.
[5] 何玮,喻凯,曾晓彬.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治理中政府 跨界协作机制研究[J].知与行,2018(4):44-49.
[6] Skinner M W,Joseph A E,Kuhn R G. Social and en- 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rural China:Bringing the changing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to focus [J]. Jour- nal of Geo Forum,2003,34(2):267-281.
[7] 李正升.从行政分割到协同治理: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 机制创新[J].学术探索,2014(9):57-61.
[8] 李胜.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基于政策博弈的分析 [J].生态经济,2016(9):173-176.
[9] Furukawa K,Okada T. Tokyo Bay:its environmental status—past,present,and future // The Environment in Asia Pacific Harbours. Dordrecht:Springer,2006.
[10] Briggs J C. San Francisco Bay:restoration progress.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2015,3:101-106.
[11] 劉畅,林绅辉,焦学尧,沈小雪,李瑞利.粤港澳大湾区 水环境状况分析及治理对策初探[J].北京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9(6):1085-1096.
[12] John A L,Charles F M. Optimal institution arrangements for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n a Second-Best World: Evidence from a differential game with asymmetric player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1,42:277-296.
[13] 金太军.论区域生态治理的中国挑战与西方经验[J].国 外社会科学,2015(5):4-12.
[14] MIRUMACHI N. Transboundary Water Polit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 Abingdon:Routledge,2015.
[15] 刘田原.论地方环保立法的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J].山 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4):65-70.
[16] 丘川颖,易清.大湾区水污染防治的立法协同机制探究 [J].政法学刊,2019(5):58-64.
[17] 曹芳.流域水环境协商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29-33.
上一篇:工业废水COD不合格的处理方法
-
华东师大|国家治理④ 疫情防范社会应急治理体系完善之策2024-08-19
-
我国农村污水治理现状及治理对策分析2021-01-09
-
总投资11.44亿元!三峡基地发展联合体中标湖北省兴山县香溪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2021-01-07
-
美尚生态:联合体签订滁河流域(来安县汊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二次)施工总承包2021-01-07
-
王圣瑞:滇池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要点在于升级提效(上)2021-01-07
-
合计1.32亿!海南省2021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分配情况公示2021-01-07
-
河道治理工程及环保措施探讨2021-01-07
-
纳污坑塘黑臭水体治理技术方案2021-01-06
-
邢台市1月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方案出炉2021-01-06
-
安徽省住建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度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重点工作的通知》2021-01-06
-
中交、长江环保集团等4方入围7亿元湖南省渌口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工程PPP项目2021-01-06
-
废气吸附效率“环保账”:优质炭≥劣质炭的4倍 治理成本降20%!附官方解读2021-01-06
-
大气治理行业政策及环境分析2021-01-06
-
2020年水污染治理行业发展评述和2021年发展展望2021-01-06
-
《温州市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发布2021-01-05